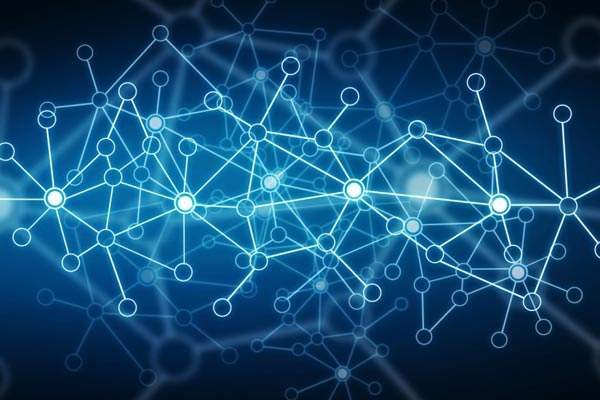時間:2021-12-24|瀏覽:394
元宇宙的話題近來非常之熱,要對這個話題做足夠深入的討論,需要進入到關于人類秩序的一些深層探討。現在網上對于元宇宙的討論,太多就像是對冰山浮在水面上那十分之一的描述,但沒有水面下的那十分之九——也就是內在于人類秩序的一些基本邏輯——這十分之一根本就浮不起來。本文嘗試從那十分之九的水下部分談起,最后再來談那水面上的十分之一。

01觀念與時代的錯位;從人類秩序的角度來看,當今正處在一個劇烈變遷的時代。劇烈的變遷會讓人們感到困惑、混沌、無所適從,因為這種時代充滿不確定性。劇變時代帶來不確定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技術變遷已經把人們不自覺地帶入到一個新的時代,但人們卻還是在以上一個時代的觀念來看待問題。新的時代不服從上一個時代的邏輯,基于上一時代的觀念所形成的預期,在現實中會屢屢落空,不確定性便浮現出來。
這種狀況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開啟了地理大發(fā)現,開始航行于曾被視作幽溟的遠海,到達此前未知的大陸,獲得前所未有的財富。然而,西葡兩國仍然是站在陸地的觀念下來理解大海的。在陸地視角下,財富的根基在于土地,所以大航海的目的就是占領遠方更多的陸地以獲取財富;大海則是通達遠方陸地時必須要克服的障礙,而不是把世界聯(lián)通為一體的大道。所以,兩國竭力去海外占領了大片的土地,也獲取了大量財富;兩國還聯(lián)手推動教皇在1493年對地球進行劃分,然而,海洋上有著與陸地上截然不同的秩序邏輯,西葡兩國試圖把陸地上的法律邏輯平移到海洋上,注定會失敗。
后起者英國、荷蘭到海上冒險的時候,最好的土地已經都被西葡占取了;基于西葡兩國瓜分兩個半球的法律,其他國家如果不經西葡兩國允許就到海洋上去冒險,屬于海盜行為,英荷等國進一步被擠壓著海上的空間。兩國被迫轉換視角,不再是站在陸地上看海洋,而是轉到海洋上看陸地。視角一旦轉換,海洋就不再是需要克服的障礙,而是聯(lián)通全球的大道;財富不再是基于土地,而是基于通過海洋完成的貿易。所以,英荷等國不再以海外占有土地作為目標,而以占領咽喉航道的據點為手段,以稱霸海洋為目標。這開啟了一整套全新的戰(zhàn)略邏輯,以及相適應的全新政治-經濟邏輯,英荷等國終于逆風翻盤。率先開啟了海洋時代的西葡兩國因為觀念的滯后,并未能真正地統(tǒng)治海洋。我們不應嘲笑兩國的觀念與時代相錯位,因為早期的英國并不比它們高明,只不過是被西葡兩國搶占了海洋先機,英國被迫另辟蹊徑,結果反倒打開了全新的局面。
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當中,觀念與時代的錯位帶來了大量毫無意義的殺戮,并進一步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埋下了種子。直到19世紀中后期,歐洲人的戰(zhàn)爭仍然有著貴族氣質,講求勇氣與紀律,戰(zhàn)爭中對峙的雙方,都會對于這種貴族氣質有著足夠的尊重與默契,相互也會留出足夠的體面。19世紀歐洲大國間的最后一場戰(zhàn)爭是1871年的普法戰(zhàn)爭,普魯士依憑新建成的發(fā)達鐵路系統(tǒng),完成了過去難以想象的動員效率,摧枯拉朽一般擊敗了法國;這個戰(zhàn)爭過程已經與傳統(tǒng)戰(zhàn)爭不一致了,但主導普魯士的是老貴族俾斯麥,他依從其階級本能,在戰(zhàn)勝之后也給法國留出體面,雖然在物質上要求了割地和巨額賠款,但是并未從尊嚴上羞辱法國。
普法戰(zhàn)爭之后開始了第二次工業(yè)革命,重化工業(yè)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展開,工人群體的規(guī)模前所未有地擴大,他們強烈地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利,歐洲各國陸續(xù)進入到大眾民主的政治形態(tài)。重化工業(yè)重新定義了戰(zhàn)爭,從此之后,戰(zhàn)場上最核心的不是勇氣,而是你有多少挺馬克沁機槍;大眾民主重新定義了政治,貴族式的體面不再是政治中不言自明的默契,充滿技巧的政治動員才是掌握權力的根本竅門。然而,歐洲人的觀念并未足夠地跟上時代的變遷,結果就是,在大眾政治的狂熱中,歐洲懵懵懂懂地走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
歐洲各國的軍官多半是貴族出身,他們仍然從貴族傳統(tǒng)所理解的勇氣與紀律出發(fā)來設定戰(zhàn)術與戰(zhàn)法,命令士兵排成整齊的隊列無畏地向前推進。但是面對鋼鐵制造的馬克沁機槍,貴族傳統(tǒng)式的勇氣與紀律變得不值一提,無畏推進的戰(zhàn)士們被機槍火舌無情吞噬,高峰時期甚至每天死亡幾十萬人,戰(zhàn)爭當中看不到勇氣與激情,只剩下毫無意義的殺戮。德國在堅持了四年之后,由于耗盡了資源而決定投降,此時德國國土上沒有一個外國士兵,相反,它的大軍都駐扎在外國領土上。德國因此而期待著投降后能獲得體面的對待,就像1871年它對待法國那樣。但是大眾政治不再有老貴族的那種階級本能,在一戰(zhàn)后的凡爾賽會議上,他們要的不是給對手以尊嚴,而是狂熱的報復,并要對對手在道德上做貶低、羞辱,以便免除自己在壓榨對手時可能會有的心理負擔。這樣一種羞辱,激起德國更強烈的報復心理,終于引發(fā)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技術與失衡
觀念與時代的錯位,背后反映的是一系列失衡,失衡經常又是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人類的秩序就是一種均衡。人們在給定的資源約束下,找到一種自我組織起來的方式,并且人們對這種組織方式的正當性有著普遍性的認可,均衡的秩序就成立了。生產技術的進步,會帶來大量新的物質財富,“給定的資源約束”變化了。新的物質財富不會是平均分配的,往往是過去的失敗者才有機會抓住新的機會,因為他們本來也無可失去,不如索性在新機會中奮力一搏;過去的成功者則會對于既往成功的經驗有著路徑依賴,反倒無法及時抓住新的機會。物質財富分配與政治-社會關系的結構,不再有均衡,人們過往自我組織起來的方式就此會遭遇挑戰(zhàn)。
知識生產和傳播技術的進步,會帶來對于正當秩序的新想象,以及帶來這種想象的社會擴散。同樣的一種秩序,在過去的觀念想象下是可接受的,在新的觀念想象下就不再可接受。在舊觀念下,人們對于既有的秩序是滿意的,沒有改變它的動力;在新觀念下,人們則可能會充滿了改變的動力,隨著新觀念的傳播,這種動力就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歷史進程。進一步來說,物質層面的失衡,精神層面的失衡,最終都可以歸結為觀念上的失衡。技術已經呼喚出了新的時代,但人們在觀念上仍然停留在上一個時代,應對失衡的方案與策略可能就是南轅北轍,甚至引發(fā)更大的失衡,引爆更大的問題。
進步就是重建均衡從前面的邏輯上來說,所謂進步就是重建均衡,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點,又是觀念上的升維。技術進步驅動著新的財富和知識的出現,但倘若這些新的東西還未獲得精神自覺,沒有從本質上梳理清楚自己究竟意味著什么,則此時還沒有形成新的秩序,而僅僅是出現了新的要素,不過這些新要素通常是有著傳統(tǒng)秩序難以想象的巨大成長性。此時也不是說傳統(tǒng)秩序就不存在了,它通常會以某種形式成為人們突進到新的要素世界時所依憑的基礎設施;但是傳統(tǒng)秩序與新要素之間又可能有著各種激烈的沖突,也就是說,基礎設施和上面的應用可能會有各種不匹配。如何能夠安頓激烈沖突的傳統(tǒng)秩序與新要素,并導向新的秩序呢?這就需要一種觀念層面的升維。
面對西葡兩國對于海洋所提出的主權要求,國際法之父、荷蘭人格勞秀斯在1605年提出了“海洋自由論”,論證了海洋因為無法像陸地一樣被實際占有,從而服從的是完全不同的秩序邏輯,海洋是自由的,服從自然法,而不服從哪個國家的主權法律。海洋秩序就此開始獲得精神自覺,它不再是冒險家在上面搏命的充滿偶然性的賭場,而是開始能夠形成一種內含著法律確定性的擴展秩序。平行于陸地秩序的海洋秩序浮現,并以其超強的增長性,通過基于海洋的貿易邏輯,把傳統(tǒng)的陸地秩序也整合進來,促動著后者的自我改造與演化。格勞秀斯通過觀念升維,帶來了海洋與現代世界的精神自覺,重塑了超越陸-海的秩序均衡。
面對著一戰(zhàn)后在凡爾賽和會上屈從于民族主義狂熱,瘋狂壓榨德國的戰(zhàn)勝國群體,凱恩斯冷靜地提出,如果向德國壓榨巨額賠款,德國便只能靠大規(guī)模出口獲取硬通貨,來支付賠款,而德國的出口擠占的都是戰(zhàn)勝國市場,德國賠款付清之日也就是戰(zhàn)勝國滅頂之時;如果為了避免這個可怕后果,便不許德國出口,它就沒有能力付出賠款,不給它付款的能力,卻壓榨巨額賠款,和約便成了對于德國的無盡羞辱,這種羞辱不會帶來和平,只會帶來下一次大戰(zhàn)。為了避免和約帶來的這個前景,必須要超越民族主義,找到一種超國家的制度方案,來把德國引導到一個更加可欲的戰(zhàn)后秩序當中。凱恩斯設計的超國家方案,構成了世貿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原型,也構成了馬歇爾計劃的原型。可惜在一戰(zhàn)后的民族主義狂潮中,沒有人理會凱恩斯,終于導致了二戰(zhàn)。二戰(zhàn)行將結束之際,人們想起凱恩斯在20年前曾經給過一整套方案,于是終于肯把這套方案付諸實施,構建了二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礎。
互聯(lián)網與人類秩序
觀察歷史是為了理解當下。當下的世界又處在巨大的不均衡當中,我們需要看清是什么技術在造成這種不均衡,未來又需要如何升維。促成這種不均衡的技術就是廣義的互聯(lián)網技術。互聯(lián)網并不僅僅是個技術,它更是對人類秩序之演化邏輯的一個技術模擬。在人類秩序中,我們可以看到兩種路徑,一種是自下而上分布式生成的自生秩序,還有一種是自上而下集中式生成的建構秩序,但任何一個建構秩序都要在與其他多個建構秩序彼此之間不斷的博弈、磨合的過程中展開,磨合出來的結果仍然是一個自生秩序,建構秩序只不過是這更大的自生秩序內部的參與者之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社會的秩序在本質上而言就是一種分布式決策、分布式運動的過程,通過各種各樣的分享、互聯(lián)、重組等等,聚合為世界秩序。互聯(lián)網剛好就是對人類秩序這種演化邏輯的一個非常漂亮的技術模擬。
更進一步,因為互聯(lián)網在重新構造人類相互之間的連接方式,也就是在重新構造“給定的資源約束下,人類自我組織起來的方式”;同時,互聯(lián)網上有大量的新觀念,觀念的傳播速度也是前所未有地快,人們對于正當秩序的想象模型也就在不斷地迭代演化,新的想象模型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飛快傳播。這些都使得,互聯(lián)網技術讓人類秩序的演化節(jié)奏大幅加快。
上世紀90年代末互聯(lián)網開始大規(guī)模興起,到現在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世界已經變得面目全非。這毫無疑問會帶來大量不均衡,同時,我們的觀念更是會大幅落后于這個時代。所以迄今為止的互聯(lián)網世界仍然處在秩序的混沌期,混沌期的意思是說,互聯(lián)網世界還未獲得精神自覺,從而仍不構成新秩序,而僅僅是一些仍然內含著各種偶然性的新要素而已;如果不能找到新要素與傳統(tǒng)秩序之間的恰當關系,則新要素的成功便無法獲得法律確定性,傳統(tǒng)秩序也會在與新要素的各種沖突中,遭遇到各種傷害。直到我們能夠足夠地升維,從更高視角來同時俯瞰新要素與傳統(tǒng)秩序,找到統(tǒng)合兩者的邏輯,新的秩序才真地浮現出來。
具體該如何升維,目前還說不清楚,人們也還是在混沌中進行著各種摸索。但如何在混沌中摸索,也有其方法論。首先就是要對混沌的對象進行分類,從中找出新秩序的潛在可能性。(廣義的)互聯(lián)網構造著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數字世界,但這個數字世界內在是分層次的。這里所謂的層次不是高低之分,而是以其與傳統(tǒng)世界的距離遠近來劃分。
1、近幾年來我們不斷可以聽到一句話,“所有的行業(yè)都值得重做一遍,以互聯(lián)網的方式。”數字經濟再怎么發(fā)達,仍然需要線下的各種實現,這些線下實現必須依托于傳統(tǒng)產業(yè),所以傳統(tǒng)產業(yè)是不可能消亡的,沒有夕陽產業(yè),只有夕陽做法。傳統(tǒng)產業(yè)在今天必須以互聯(lián)網(這里說的是廣義互聯(lián)網、包括物聯(lián)網在內)的方式重構自身,否則將難以獲得行業(yè)本身的生產效率,也難以獲得進入市場的渠道,不能參與進來的企業(yè)就會在這個過程中被淘汰。
這里我們就看到了與傳統(tǒng)世界有著最緊密關聯(lián)的數字領域,物聯(lián)網,以及各種設備生產商、運營商等等,都是數字世界與傳統(tǒng)世界的接口性存在。這是數字世界的第一層次,這個層次的運轉都是基于實體經濟,實體經濟依托于特定的物理空間,從而也就與主權國家之間有著各種各樣的關系,甚至可以說,主權國家在這個層次上有著相當的主導性。
2、第二層次的數字世界則進入到了虛擬經濟,但這是一種非分布式的數字世界。過去的十幾年中,谷歌、臉書、亞馬遜、阿里、騰訊、字節(jié)跳動等等一系列的數字巨頭,營造出了一個龐大無比的數字世界,虛擬經濟所制造的財富規(guī)模及其增值速度,在傳統(tǒng)世界完全是無法想象的,令人目瞪口呆。這些數字巨頭在其所推動的內容生產上,毫無疑問是分布式的,全世界無數的網民都在參與內容和數據生產;但網民都是在數字巨頭提供的平臺上活動的,數字平臺本身的管理則是集中式的。說得極端一點,這些數字巨頭是可以拔網線的,臉書在2020年就曾經對澳大利亞政府拔過網線。所以,第二層次的數字世界由數字巨頭主導。